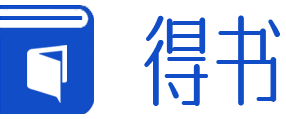导读
- 《西西弗神话》
-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 类别:
- 本章字数:1707
工业社会中,人被曾经掌握在手的技术所规定,开始的时候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一切,我们从来没有细想过。但是突然之间,会有人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觉得并非都是如此理所当然。对于平常人来说,这种异样的感觉只是一闪而过。但在戏剧化的舞台上,我们可以对荒诞之人面对的分离加以浓缩,并且将之演绎为逻辑的推理。加缪因此为默尔索创造了杀人的环节。默尔索因为杀了人,进了监狱,想明白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才进的监狱,他在精神上被他人择了出去,自己也主动把他人都择了出去,于是默尔索清楚地看见了布景与自己的存在之间的这份距离,并有意识地将坍塌下来、不再能默默吞没自己存在的布景放置在了对面的位置,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地冲上去。我们平常人并没有机会成为荒诞之人,因而也不会因为这种突然之间的发现打破日常生活的常轨,爆发出如默尔索一般的巨大激情——倘若从这个意义上说,荒诞的情感的确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
加缪的可贵之处,或许正在于他将非理性的激情与理性的推理连接起来。如果说,荒诞的命运是任谁都回避不了的,也并不因为清醒的认识就可以避得开,那么加缪在开始时为我们带入的就是地中海的阳光。在《西西弗神话》中,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前,是要知道生命是否有意义,值得我们活过。而此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生命很可能没有意义,它才值得更好地活过。经历某一种经验,经历命运,就是充分地接受它。但是倘若我们不竭尽全力,充分掌握通过意识显现出来的这份荒诞,就无法经历这我们已知是荒诞的命运。”
迎着命运而上,无论在“荒诞”三角,还是“反抗”三角里,都是加缪为我们确立的存在的态度,也是他嫁接在西西弗这个形象上的人类应有的态度。巨石的滚落就好像人的必死性。然而,除了平静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命运的挑战之外,人还有更好的昭示尊严的途径吗?纵使人类几千年来累积的智慧还不足以抵挡诸神霸道而无理的惩罚,但人类运用智慧完成的一件又一件的创造本身,用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的话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反抗。
人不也是在创造中对自己的存在负起责任的吗?当堂吉诃德走出家园,从此告别了那个由上帝,由神,或者由任何一个先验的权力来规定何为人类美德的世界,他最大的野心和西西弗的一样,是迎来一个真实的世界。为此,他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原先那个虚无的美德世界的惩罚。人的这种创造的态度,被加缪称为希望。人是不幸福的,这千真万确;但另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相是,即便如此,人从来没有停下过追求幸福的脚步。当加缪写下“我从荒诞之中得到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时,当加缪引述整个20世纪为之倾倒的尼采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力”时,当加缪借用西西弗总结道,“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时,我们还有任何理由不跟随着加缪的逻辑,不将《西西弗神话》看作是“最为有效的反抗”吗?
否则,又如何解释加缪已经离世六十年后的今天,人类再次面临命运的巨大考验时,我们有不堪,有挣扎,有怯懦,有痛苦,但我们也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为了人类继续存在下去而努力地活着。如果看到这一点,加缪应该也觉得是幸福的吧。因为是在努力活着的过程中,人类终于翻转了荒诞命运之牌,获取了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由。
最后一点想要说明的是,如果说《西西弗神话》的写作和出版是在加缪的严密计划里,重译《西西弗神话》却本不在我的计划之中。《西西弗神话》已经有若干个版本,仅我读过的就有专攻法国哲学的杜小真先生的版本,文字洒脱的李玉民先生的版本,以及译风严谨、一向在准确与优美之间应付自如的郭宏安先生的版本。这或许也足以证明加缪的魅力吧:时间流逝,他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艺术创造中所提出的问题却越来越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并且空间之大,一个译者难以穷尽。我是在这些年越来越强烈的想要亲近加缪的愿望中突然受到了浦睿文化的邀约。中间也曾想过放弃,但一则有浦睿的坚持,二则也是想回应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所说的“坚持、敏锐是最为恰切的观察者”。我不知道我的坚持是否有价值,但希望在此表达对前面诸个版本的译者的敬意,因为是他们让我爱上了加缪,并且懂得了坚持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