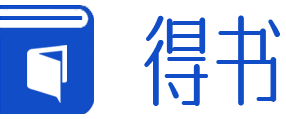自序
-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 作者:[美]陶涵
- 类别:
- 本章字数:2222
自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九岁之龄(官方公布为虚岁)逝世时,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由于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太加注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蒋氏过世之时,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一般公认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佩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
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撰写蒋氏的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偶像。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按一般的看法来描述这位父亲。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一书出版之后,又要求我为蒋氏本人写本传记,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我忖思良久。虽然我对蒋氏的看法大半属于负面,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我想我能够开明地处理好这个主题。
我又受到若干学者的鼓励,他们证实了我的印象;近年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档案材料,但西方还没有人善加利用写出一部丰富而完整的蒋介石传记来。中国学者则利用这些素材,就蒋在大陆和台湾长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国内外动态关系,已写成数百篇有见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蒋家后人也开始陆续公开蒋氏长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记。
通过新的访谈,加上我以前撰写《蒋经国传》时所作的准备,结果我引用的访谈过的相关人士有几百人——许多人也认识蒋介石。只不过这些人士上了年岁,交谈的机会恐将不再,因此集结这些材料来源,似乎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项计划。此外,就像他儿子的传记,我也将这本新书视为一个独特的工具,述说中国痛苦、动荡不安的历程,从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受满族统治的腐朽旧王朝,到百年之后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快速繁荣强盛的国家。
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个现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径。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与羞辱,可是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所有的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颇受爱戴。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但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从日记分析,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临对国家存亡、统一或他本身统治地位的威胁,他会不惜诉诸残暴手段。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机又往往能够冷静分析事理,反映出他了解当前问题的动态和可能性。在大陆,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大溃败。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作好准备。
蒋的日记让我们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他意外蹿升为国民党领袖,他早年的左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军阀一再兴兵作乱,他一面建军一面对日姑息历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遭到劫持,国共联合阵线的过程与破裂,他和周恩来长久的特殊关系。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他在淞沪保卫战及其后的军事策略,他和斯大林相互使劲把对方卷进对日战争,他和史迪威将军的长期斗争,以及在珍珠港事变后他对盟国严正的军事承诺——然而盟国的不断失信以及他仔细盘算却又不智的回应,都让这份坚贞大打折扣。
战后的大事则包括: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蒋错误决定在东北孤注一掷,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计划退守台湾。最后,蒋氏日记和其他新材料也对他撤守台湾后,提供早先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他对台湾本省潜在的反对势力进行残暴、无情的威吓和弹压,国民党内不满他领导的种种风波,他对朝鲜战争、越战的悲观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光复大陆”,可又一再公开宣布即将“反攻”。他利用这些警告从华盛顿得到特别待遇,同样成功的,还有将两次濒临核战边缘的金门危机扭转成自己的优势,以及拒绝艾森豪威尔一项可能导致美中大战的危险提议。
后来还有许多重大事件相继出现,但是蒋氏在他生前最后的重大危机中倒回应得很务实——其中之一就是隐藏他对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修好,他显然先从周恩来那里得知的。现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领导人能像蒋一样长年居于最高位、积极参与缔造历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纪录恐怕也非后人能及。基于这个理由,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他的故事大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