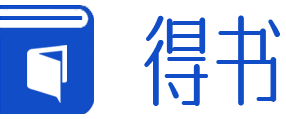三
- 《乌合之众(译文经典)》
-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
- 类别:
- 本章字数:1999
在对群体的讨论中,勒庞更多表现出否定态度。但在《乌合之众》的下篇,当重点讨论重罪法庭陪审团等有名称的异质群体时,勒庞却表现出少有的肯定姿态。或许,正是法国司法史上反复不断的冤案,尤其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德雷福斯事件”,让作者持这种保留意见。我们知道,在《乌合之众》出版前一年,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革职后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岛遭终身监禁。随后不久,尽管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依然竭力维护误判,而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在谈到法官误判和诸多特殊案例时,勒庞充分肯定了陪审团制度的优点,并给出如下论断:“它或许是个体唯一不能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削弱法律的严酷。尽管法律原则上人人平等,但它对特殊情况却视而不见。”谈到这里,读者无疑对2016年“辱母杀人案”在国内激起的全民热议记忆犹新,该案最终以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五年监禁画上句号。以此看来,如何在维持社会公正的前提下,让铁面无私的法官“法外开恩”,正是“感情用事”的陪审团理应担当的角色。
随后,在讨论选民群体和议会团体两个异质群体时,勒庞再次强调了它们具有思维简单、不加推理、缺乏批判、领袖作用巨大等普遍群体特征。针对各国普遍采取的选举制度,勒庞一方面犀利地指出了选举中存在的潜在贿赂问题,因为财富可以取代声望为选票买路;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揭露了候选人为赢得选票,事前天花乱坠地空口承诺,事后全然不加兑现的无耻嘴脸。对于各国政府实施的议会制度,尽管同样存在种种弊端,但这种群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勒庞看来有别于其他群体。因为起草法案的都是个体专家,所得必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全面的考查。只要议会上不对这些法案条例进行过多修改,这种制度依然是最佳的统治模式,因为它有效避免了个人独裁专制的出现。
诚然,在撰写《乌合之众》时,勒庞主要以法国大革命的诸多事件为例,并且直言不讳地评判拿破仑、罗伯斯比尔、丹东等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跨度较近的事件和人物,他则很多时候只是含沙射影,诸如书中“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一份据称有辱法国大使的电报公之于众”等说法。这种避讳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做法,无疑侧面反映出勒庞的谨慎与保守姿态。不过,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勒庞,在以史为鉴告诫群体暴力导致的可怕后果时,却提议“应当把史书视为纯粹想象的产物”,矛盾地否认历史的一切价值。
其实,勒庞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反映出人们学习历史但从中不得教训的矛盾,而且人们对于历史上重大运动的遗忘速度之快更令人惊讶不已。在谈到这一点时,汉娜·阿伦特认为“集权主义运动遗忘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而且轻而易举就可以被另一种运动取代”。对于重大创伤性历史事件的遗忘,其机制不像弗洛伊德提出的个人对于创伤事件的“屏蔽记忆”,而是显然又验证了黑格尔那句反讽意味十足的名言:“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悲剧才会不断反复和重演。毫无疑问,面对声势浩大的欧洲革命,作者在《乌合之众》中透露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的忧患,这与后来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表露的悲观色彩如出一辙。
一本书受人追捧、畅销一时容易,但要经历时间考验成为经典尤难。在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中,作者看似只“研究群体的精神”,实则提出并讨论了那个时代乃至我们当代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群体的盲从与反叛、民众运动、集体无意识、应试教育弊端、商业广告、演说成功要素、政府开支与官僚化、人的异化与冷漠等一系列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墨顿所言,正是这本书“涉及问题的多样性,使它具有持久的意义”。由此可见,我们今天阅读勒庞的这本百年经典,仍然会帮助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保持敏锐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
当今的社会形势更为复杂,在经历百年以大众运动为特征的群体时代之后,我们多少又迈向了标榜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个体时代,或者更多是两种局面共存于世的对立形势。面对网络信息时代的喧嚣,如何在民众意见的洪流中保持冷峻的个人头脑,避免人云亦云;面对个体意识的过度发展,人们日趋冷漠和孤立,该如何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今,我们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不是宣扬反集体主义思想,误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而是要留存个人的批判精神,驾驭群体的威猛力量,并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绝妙的平衡,从而确保人类数万年的文明可以永世长存,而避免走向勒庞书末预言的那种宿命的衰亡。
∗∗∗
在重译《乌合之众》的过程中,我立足于法语原文,认真研读作品,翻译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锤炼,力图达到严复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此外,我在翻译中还借鉴了该书的英译本,多方考证,扬长避短,以期准确传达原文的精神风貌。当然,本人的法文直译本质量到底如何,还有待读者朋友在阅读后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