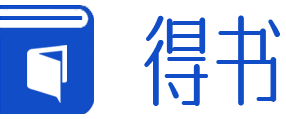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
- 《为什么是中国》
- 作者:金一南
- 类别:
- 本章字数:1812
舰队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比如,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典型的“演为看”,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搁浅损毁,“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是清军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却上报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报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北洋舰队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皆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终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了“‘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人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便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卫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
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结果“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曾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