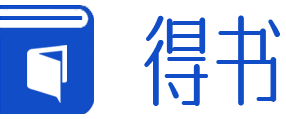作者自序
- 《人性的枷锁》
- 作者:[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类别:
- 本章字数:2265
作者自序
这部小说已经够长了,还要再写篇前言来增加它的长度,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更何况,作者本人可能是最没办法对自己的作品做出恰当评价的人。关于这一点,杰出的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曾讲过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据说马塞尔·普鲁斯特想让一家法国期刊发表一篇关于他那部伟大小说的重要文章,他觉得没人能写得比他更好,于是就坐下来亲自写了一篇,然后叫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给编辑。年轻人照他说的做了。结果没过几天,编辑就把他叫了过去。“你这篇文章我不能登,”编辑对他说,“这些批评如此草率,如此刻薄,我要是把它登了出去,马塞尔·普鲁斯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虽然作者们对自己的作品都像母鸡护雏似的敏感,听不得那些不好的评价,但其实他们很少对自己的成果感到满意。他们知道自己费时良多、呕心沥血的作品跟脑海中的构想相差有多远。每念及此,他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对自己言不尽意的懊恼,而不是对个别段落言尽其意的自得。他们追求的是完美,而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实现它。
所以我不会对这本书本身做任何评价,而是满足于告诉这篇文章的读者,这部就小说而言已经称得上长盛不衰的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如果读者觉得乏味,我请求你们的原谅。第一次提笔写这本书时我二十三岁。那时我结束了在圣托马斯医院五年的学习,拿到了医学学位,动身去了塞维利亚,决心以写作为生。当时的手稿现在还在,只是自从我校对完打印版后,我就再也没看过它。我也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写作还很不成熟。我把书稿寄给了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第一本书(我还是个医学生的时候,写了一本叫作《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反响很不错),可他拒绝了我一百镑的要价。后来我又把书稿寄给了其他出版商,无论我要价多少都没有任何出版商愿意出版它。这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可现在看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如果当时有人接受了我的书稿(那时候叫《史蒂芬·凯利的艺术人生》),我就失去了一个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好好把握的题材。那时的我离书中描写的事情还不够远,无法置身事外地写作;我也尚未经历后来经历的那些事情,而正是那些经历丰富了我最终写成的这本书。我也尚未意识到,写自己熟悉之事比不熟悉之事更容易。比如说,在第一本书里,我让主人公去了鲁昂学法语(而我只是在鲁昂游玩过几次),而在这本书里,我让他去了海德堡(那是我曾经求学的地方)学德语。
由于处处碰壁,我把手稿束之高阁。此后几年我又写了其他的小说,也都陆续出版了。我还写了剧本,没过多久就成为了非常成功的剧作家,并且决心把余生都献给戏剧。然而我忽略了内心深处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使我献身戏剧的决心变得徒劳。我那时很快乐,日进斗金,整日奔忙,脑海中满是想写的各种剧本。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成功并没有带来我所期待的一切,也许是因为这是成功之后的自然反应,就在我功成名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后不久,我又开始被过往生活中种种回忆纠缠。它们来势汹汹,步步紧逼,在我睡觉、走路、彩排、聚会时袭来,成了压在我心头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我认定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都写下来。戏剧创作不得不戴着手铐和脚镣,这样写了几年之后,我无比渴望小说创作的广阔自由。我知道我想写的这本书会很长,我想不受打扰、心无旁骛地写作。于是我拒绝了剧院经理们争先恐后送来的合约,暂时告别了舞台。那一年我三十七岁。
成为职业作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写作,还会逼自己做一些枯燥的训练,以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不过在我的剧本开始被搬上舞台之后,我就不再这么兢兢业业了。而当我再次提笔时,我的目标已经变了。我不再追求珠玉华章和余音绕梁——以前我在这些东西上浪费了大量心力,却总是徒劳无功;相反,这一次我追求的是平实和简洁。由于我想说的太多,又有必要的篇幅限制,我感觉一个字也不能浪费。于是我在动笔前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要求:只要能达意,只用最为必要的词语。我没有多余的空间去雕饰文辞,戏剧创作的经验也教会了我言简意赅的重要性。然后我一鼓作气写了两年。写好之后,我不知道该给它取什么名字。经过一阵漫长的苦思冥想,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美自灰烬出”这句话。这是《以赛亚书》里的一句经文,在我看来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可后来得知不久前已经有人用过了,我只好另想一个。最后我选了斯宾诺莎《伦理学》其中一卷的标题,把这部小说命名为《人性的枷锁》。我觉得失去第一个名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幸运。《人性的枷锁》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在一起:书中的悲喜孤愁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全然如书中所写那样发生过;主人公某些经历并非取材于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借用了我身边一些密友的经历。这本书确实如我所愿,让我获得了解脱。当它问世时(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世人在痛苦和恐惧中自顾不暇,哪有心情读一个虚构人物的人生经历),我发现自己终于摆脱了那些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和苦涩回忆。这本书出版后大受好评,西奥多·德莱塞为《新共和》杂志写了篇很长的评论文章,他的评价体现出了他的才智和同情共感,这正是他所有作品都具备的两大特征。不过在当时看来,这部小说还是很有可能会步绝大多数小说的后尘,问世几月之后便无人问津。然而,我也不知道是由于怎样的因缘,几年之后,这部小说竟然引起了美国许多著名作家的注意。他们不断在报刊上提及此书,逐渐让它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多亏了这些作家,这部小说才得以重获新生;我也必须感谢他们,让这部小说得以在时间的长河中越发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