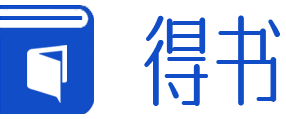传统中国的时间
- 《法度与人心》
- 作者:赵冬梅
- 类别:
- 本章字数:2216
图五: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此图俗称《四美图》,明代唐寅作,绢本设色,124.7厘米×63.6厘米。画面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后宫里的故事。画中四位宫妓头戴金莲凤鸟花冠,身着云纹装点的道衣,端庄而不失娇媚。身着蓝色衣裙的宫妓,正给左边穿褐色衣裙的宫妓劝酒,右边身着绿色长裙的宫妓,身体略微前倾在斟酒,中间背对我们的这位,左手托盘里盛放着酒壶和点心。从画面看出,左边这位宫妓已然不胜酒力,似在挥手婉拒不能再喝了,而蓝衣女子依旧在不住地劝她更尽一杯。四人相向而立,通过婀娜的姿态和推让的手臂,画面的生动感与丰富性跃然而出。唐寅以“三白法”在宫妓的额、鼻、颌三处涂上白粉,恰似如今的高光妆容,使得人物面部更加饱满立体。
有意思的是,宋太祖的乾德年号并没有立即停用,一直用到了乾德五年,直至乾德六年才把年号改成开宝。宋太祖的不信邪,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新皇帝即位的当年是不改元的,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用新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不逾年改元”者,若非改朝换代,则难免落人口实。比如,公元220年曾出现了三个年号——建安、延康和黄初。这一年本来是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曹丕嗣魏王,二月,改年号为延康(献帝年号);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又比如,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太祖暴崩,其弟即位,是为太宗。太祖自有子,且已成年,兄终弟及,“斧声烛影”,固已启人疑窦。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复下令改元,太平兴国元年只得八日。“不逾年改元”,八日都不肯等,吃相未免难看,更令人疑其皇位来路不正。
同一个皇帝换年号,有的是为了向上天祈福,比如武则天,有的是要宣誓政治路线。最喜欢在年号上标榜政治路线的,是宋朝。比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导致官僚集团分裂,新旧两党对立。神宗用过两个年号——熙宁、元丰。神宗之子赵煦(后来的哲宗)幼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一反神宗之政。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重返神宗路线,遂用绍圣做年号,“绍”者继承,“圣”者神宗,“绍圣”的意思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神宗的另一个儿子赵佶,即徽宗,用过一个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熙宁,宣誓重回熙宁政治路线。崇宁是宋徽宗的第二个年号,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意思是采用中间路线,调和新旧两党,以期重建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十九岁的宋徽宗刚上台时的政治诉求——这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看问题很准,知道国家的麻烦在于官僚集团的分裂,只可惜有心无力,好大喜功,最终还是倒向了新党一边,“崇宁”去也。
明清两代,画风大变,皇帝不再拿年号玩文字游戏了,基本上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用到寿终。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是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的,比如“洪武爷”“朱洪武”,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三位皇帝。
与年号等政治时间相关联的行为,有颁历授时。“颁”是颁发之意,“授”是授予之意,“历”就是历书,是有关年、月、日、节日、节气等的时间表。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因此,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理想就是,取缔一切民间私自制定的历书,由官方制定历书,并颁发到全国各地,让全国各级政府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工作,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生产生活。换句话说,历书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时间秩序。
传统史书把颁历授时的传统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圣王尧的时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用一本历书统一全国其实是很困难的。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历书就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终归有限,在很多地方,老百姓还在用民间学者制定的私历。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在新疆的吐鲁番,也能严格按照唐中央颁布的历书行事。按照现在的道路里程,新疆吐鲁番距离唐代长安是两千多千米,唐代的路况跟今天是没法比的,所以会更慢。长安十一月颁历,次年的二月,这份新颁的历书才能抵达吐鲁番。可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地方政府的粮料是按月发放的,每月按天数计算,大月小月差一天。在接到中央政府的历书之前,吐鲁番地方政府有两个月无历可依,那么,这两个月应当怎样发放粮料呢?一概按小月发放,待日历到时再做更正。倘若这两个月都是大月,那么就把那两天的口粮补回来。唐朝律令制政府行政的严谨性,以及唐中央无远弗届的行政覆盖能力,令人惊叹。
干支计时与颁历授时这两种传统的时间标记方式所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间观念?意义的产生需要外物的参照,我们的参照物是西方的公元纪年法。
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为界线,把时间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两部分。不管“公元前”还是“公元后”,时间都是连续的,这是西式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不管是干支,还是皇帝的年号,都处在不断的“重启”当中。六十一甲子是不断更新、重启的,每一个甲子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朝代的建立、每个皇帝的即位,甚至每个年号的开端,也都是一次重启。相较之下,中国的时间其实比较缺乏连贯性。正因如此,那些通史的写作者,比如司马迁、司马光才显得尤其伟大,因为他们让“我们的时间”连续起来了。